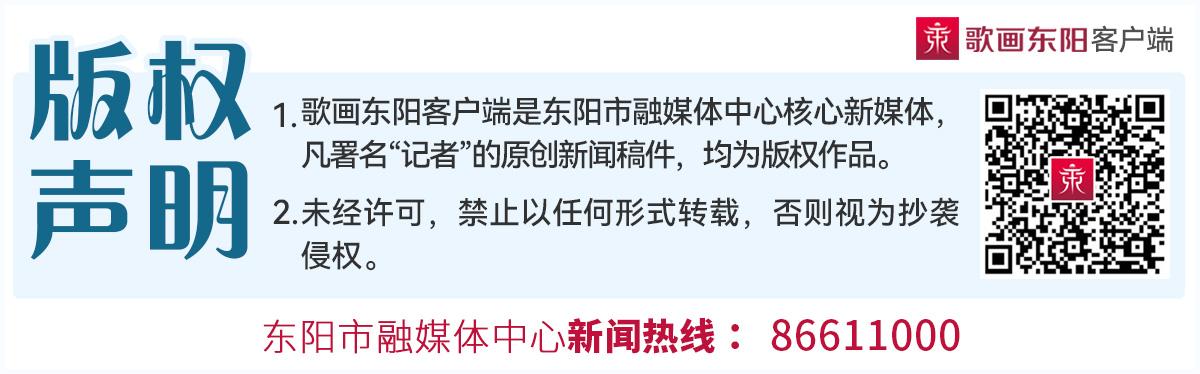歌画东阳
歌画东阳 共见精彩
“打起黄莺儿,莫教枝上啼。啼时惊妾梦,不得到辽西。”唐人金昌绪的《春怨》,句句设疑,句句作答,一浪接一浪地向前滚动,事小体大,曲尽其妙。无论摘出哪一句都不叫诗,然四句合在一起就有了另外一层意思。唐人很可爱,可谓上得了厅堂、下得了厨房,像这样的乐府诗,豪迈如李白、刘禹锡都没少写。
有学生曾问叶嘉莹先生:“老师,您讲的古典诗词很精彩,可是学了它有什么用呢?”的确,学了古典诗词既不能帮助你找工作,更不能帮助你挣钱发财。那么,为什么还要学它?叶先生认为,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你的心灵不死。如果你的心完全沉溺在物欲之中,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,那实在是人生中第一悲哀的事。诗可以使你的心活泼起来,永不衰老。这就是读诗、学诗的好处。
叶嘉莹先生站在讲堂上的意义,就在于让我们重新发现古典诗词里最触动人心的地方。
明清诗人除了杨慎、纳兰容若、黄景仁等极个别人外,我几乎没翻过其他人的集子,要我讲古典诗词,我也只能讲唐诗宋词,以及南北朝温润华美的诗章。唐诗之花为何绽放得如此美丽,为何后世再也无法超越?

读书会海报 朱洪峰设计 7月30日,“驿站”读书会在市党群服务中心重启,此文为“驿站”发起人葛煊炜的讲稿,为便于刊发有所删节。
六首诗窥探唐诗的华美和从容
我选了几首唐诗,大家一起来读。诗歌是要读出声的,声律、韵味就像经文,只有读着才入味,看诗容易一知半解。
《蝉》:“垂緌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虞世南是浙江人,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。他善书法,是初唐四大家之一。这一首托物寓意的小诗,是唐人几首最好的咏蝉诗之一,笔意很巧妙,讲品格高洁的人,不用依赖外在的凭藉,强调人格的力量。重点在第二句,元人总结说唐人很重视“起承转合”,“流响出疏桐”就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,读古诗要特别留意动词和形容词。一个“疏”字,梧桐高挺的形态就出来了。开元之初正是上坡阶段,诗人内心饱满,字里行间渗透着浓浓的书卷气。
《滕王阁诗》:“ 滕王高阁临江渚,佩玉鸣鸾罢歌舞。画栋朝飞南浦云,珠帘暮卷西山雨。闲云潭影日悠悠,物换星移几度秋。阁中帝子今何在?槛外长江空自流。”此诗放在《滕王阁序》篇末,写得很洒脱,是作者意犹未尽的无心之作。整篇诗歌是流动的,像江水那般流动,是自然生发的。但是这首无心之作不同寻常,唐诗写到这儿,就要出现一个转折了。“阁中帝子今何在?槛外长江空自流”,一开一合,自然流动。明人凌宏宪说:“只一结语,开后来多少法门。”唐诗的好是水到渠成的,从庾信到隋炀帝杨广,声韵变得更和谐,诗歌更简洁干净,只需有人轻轻一推,一种“新声”就会诞生。王勃就是这么一个推门人。
《五日观妓》:“西施谩道浣春纱,碧玉今时斗丽华。眉黛夺将萱草色,红裙妒杀石榴花。新歌一曲令人艳,醉舞双眸敛鬓斜。谁道五丝能续命,却令今日死君家。”五日是端午节,大家宴饮取乐。宴会上,乐伎美妙动人,勾魂摄魄,让一个外来者进一步则自感身世,退一步则撕心裂肺。它让我想起宋人孙洙的《菩萨蛮》:“楼头尚有三通鼓,何须抵死催人去。上马苦匆匆,琵琶曲未终。”古人是真性情,把这两首诗词放一起看,有万楚的铺排,才有孙洙的激愤。整篇《菩萨蛮》就是对万楚最后一联的酣畅敷衍。与宋人的天马行空相比,唐人更愿意写实,写实却不尽意,让人浮想联翩,“醉舞双眸敛鬓斜”,多么生动。万楚和孙洙说了别人不能说的,没有“梦中人”“梦中事”,就做不了诗人。对一首赠妓之作来说,艺术性即是思想性,并不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才有思想性,多少佳作就这样埋没在故纸堆里。这首诗张弛有度,收放自如,正是盛唐诗歌的标志。
苏轼一句“不与徐凝洗恶诗”,让我们认识了徐凝。但徐凝的诗歌并不像苏轼说的那么不堪,苏轼自己也曾忍不住去模仿人家,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最有亮色的一句“春色三分,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”,就出自徐凝的《忆扬州》:“萧娘脸薄难胜泪,桃叶眉尖易觉愁。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。”这首诗虚实结合得很完美。看六朝诗歌,满眼风景,兜兜转转,还是人间,你多看一句少看一句也不会丢掉多少诗味;再看徐凝的诗,出神入化,借严羽的话来说便是“空中之音,水中之月”,言有尽而意无穷,一个字都不能错过。我之所以选这首诗,还是为了强调那句话:没有“梦中人”“梦中事”,就做不了诗人,更得不到好诗。大凡好诗,都是妙手偶得之。
唐诗到了李商隐这儿,突然沉重起来。同样是借助环境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,烘托情思,李商隐展示了一幅阴郁的美。比如这首《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》:“竹坞无尘水槛清,相思迢递隔重城。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这是一个时代的下坡,一场秋雨,一场不遇,便让人不振如斯。李商隐的诗经得起反复看,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,唐诗写到他这里,转向了内心,似乎只有转入内心才有安稳。李商隐的诗歌告诫我们,离开生活的环境,就产生不了好诗,偶有好句子,也终究是隔了一层。“秋风吹渭水,落叶满长安”,和贾岛有何关系?像李商隐的这首诗,放在盛唐甚至是中唐,都是无病呻吟。写诗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
韩偓这名字大家未必听说过,但李商隐的“桐花万里丹山路,雏凤清于老凤声”这句诗肯定熟悉,这首诗中的“雏凤”说的就是韩冬郎韩偓。韩偓有一首《寒食夜》:“恻恻轻寒剪剪风,杏花飘雪小桃红。夜深斜搭秋千索,楼阁朦胧细雨中。”唐人写过很多寒食诗,后人说“读尽唐人寒食诗,人于此日重伤悲”。在唐各个时期,诗人的思绪是不一样的。把同题材不同时代的诗放一块读,能更好地理解诗人的感受。万楚写端午,韩偓写寒食,一个在盛唐,一个在唐末,气象完全不同。韩偓和李商隐也不一样,李商隐生活的朝代还有中兴的可能,到了韩偓成年时,已经病入膏肓,无药可救,反映在诗中也就有了难以置信的平静。
为什么选这6位的诗?看一个群体的好,不仅要看顶层,还要看基层。这6位诗人生活的时代分别处在初唐、盛唐、中唐和晚唐。这几首诗歌一看就知道是唐人写的,不管出在哪个阶段,唐诗的体征都很明显。
我集了一首诗,虽然仓促(有两个“未”字),但设为一个流放者的望乡之作也是蕴藉深刻。
北山烟雾始茫茫(初唐 王勃),万里还乡未到乡(中唐 卢纶)。欲就洞庭赊月色(盛唐 李白),未妨惆怅是清狂(晚唐 李商隐)。
这4句诗的作者都有代表性,每一句诗都有浓郁的时代气息,然放到一起,集成一首望乡诗,就未必看得出来。没有别的原因,就因为这是唐代诗人的作品。唐诗的那份华美和从容是这个群体的特征,刻在所有人的骨子里并贯穿始终。
唐诗的平和气质和含蓄之美
论气质,唐诗和魏晋南北朝的诗歌是一脉相承,然唐人更趋平和。试举两例:
先看南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《登作乐山诗》:“修路轸孤辔,竦石顿飞辕。遂登千寻首,表里望丘原。屯烟扰风穴,积水溺云根。汉潦吐新波,楚山带旧苑。壤草凌故国,拱木秀颓垣。目极情无留,客思空已繁。”
再看陆机的《赴洛道中作》之二:“远游越山川,山川修且广。振策陟崇丘,安辔遵平莽。夕息抱影寐,朝徂衔思往。顿辔倚高岩,侧听悲风响。清露坠素辉,明月一何朗。抚枕不能寐,振衣独长想。”
两首诗都写得很讲究,讲的是气势,讲的是雷霆万钧中的那份自在。王夫之说刘骏的《登作乐山诗》“有英雄气”,但像潘岳的《悼亡诗》一样,看上去都不是那么感人。对“物”的反复铺陈,使得任何情绪都被淡化了。看似淋漓尽致地挥洒,讲究的却是将拳拳深情融入优雅的风度。这是六朝特色,时代使然。
再看唐诗,“散发承夕凉,开轩卧闲敞。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。欲取鸣琴弹,恨无知音赏。”孟浩然的这首诗意气流转而不露痕迹。由南北朝对自然之物的膜拜,转化为唐人对内心的慰藉。因此,唐人的开放是由内向外的,是真正的开放,这就多了一份包容。
论个性,唐诗直抒胸臆的少了,更注重弦外之音。三曹、左思、鲍照的诗,拿在手上,都有分量;唐诗不同,“宛在水中央”,不能确定是何感觉。窃以为,南朝刘勰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含蓄美,“辞约而旨丰,事近而喻远。”对比魏正始前后的诗歌就会发现,自正始开始,阮籍他们说话就变得吞吞吐吐了。诗歌写得含蓄,读者就要有“悟”的能力。含蓄美不是唐人的发明,但差点成了唐诗的专利,意在言外,沉郁深微。
宛转如李益的《洛桥》:“金谷园中柳,春来似舞腰。何堪好风景,独上洛阳桥。”篇幅稍长如李白的《夜泊牛渚怀古》:“牛渚西江夜,青天无片云。登舟望秋月,空忆谢将军。余亦能高咏,斯人不可闻。明朝挂帆席,枫叶落纷纷。”
魏国的何晏王弼之流,穿的都是很宽大的衣服,两只袖子几乎垂到地面,他们做人和穿戴一样,“宽而有制,从容以和”。前人说唐诗“羚羊挂角,无迹可寻”“不着一字,尽得风流”,唐人运用这等表现手法就像魏人穿衣服一般平常。
古人将诗歌语言的含蓄美称之为“隐”。这两首诗意象和意境蕴藉深刻,启发性与暗示性都很强,极具内在张力,像壶中天地都让诗意给撑满了。
在安静和忘我中寻回内心的诗意
上面讲的是唐诗的特点和特征,但我们学不来。为什么我们达不到李白“登舟望秋月,空忆谢将军”的空明心境?为什么心中的诗意会荡然无存?难道仅仅像叶嘉莹先生说的,不是我们生活在缺乏诗意的时代,而是物欲太强烈,我们缺乏去发现?
显然,我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唐人和唐以前的人们。像宽袖缓袍的何晏王弼之流,无论何时何地,都能让自己静下心来。
还是以王勃为例。《滕王阁序》中的名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纵观整个唐朝,壮景赋色,没有任何诗句超越了它。写过古体诗词的人都有这个体会,不在诗中,写不出好诗。何为“在诗中”?俄罗斯诗人布罗斯基在《献给约翰·邓恩的大哀歌》里写道:“约翰·邓恩睡了,周围的一切都睡着了/睡着了,墙壁,地板,画像,床铺/睡着了,桌子,地毯,门闩,门钩,整个衣柜。”没有任何杂念,只有一个天地,只有一种声音,无限广大,无比逼仄,身处其境,才叫“在诗中”。写《滕王阁序》时,王勃眼里哪还有人?所有的动静都裹在了衣袖里。有些人平日里见人就脸红,但临到创作,便没了任何顾忌。在热闹的场合,收得住心,方能逞能,方能稳住天地。“忘我”不仅仅是投入,更是一种精神。
这就是唐以前的人的创作状态,内心波澜壮阔,付之笔端,是“欲持一瓢酒,远慰风雨夕”,举重若轻,一片空明。没有刻在骨子里的那份骄傲,不可能有如此深刻的平静。由深刻的平静而生发的盛衰无常、人世沧桑之感,是今人读唐诗最大的困惑。
士族骄傲撑起唐诗家国情怀
为什么我们后来的人突然丢失了这份骄傲,这份深刻的平静?
自唐朝以降,我们突然失去了一种身份。
唐朝的诗人,不管在朝在野,大多出生贵族豪门,虞世南、崔颢、韩偓等人无一不是。李商隐出自陇西李氏姑臧房,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。但在他出生时,门庭早已冷清,父亲死得早,他是家里的老大,只能“佣书贩舂”。李商隐虽然家道中落,但他的门第放在那里,依然是士族。唐人拥有浓郁的氏族情结,重视氏族婚姻,“五姓七家”之间互相通婚,五姓排名第一是崔氏,第二是卢氏。李世民的侄女婿薛元超抱怨说人生有三恨,其一就是“不得娶五姓女”。这种氏族文化是门阀制度的余风。
科举制诞生之前,门阀士族凭借家世出身就能参与朝政。门阀士族成型于秦汉,历史上最有名的便是关陇集团,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都是这个集团的成员,相互联姻,连枝同气。唐朝的科举虽然为寒门子弟开放了仕途之路,但上品高官依然多为世家子弟,寒门出高官很难得,崔卢王郑杜等家族几乎把持了相权。
东阳在唐朝出过十几个进士,厉文才是最早考中进士的;冯宿兄弟子侄有“祖孙九进士,兄弟两尚书”之誉;舒氏则兄弟4人联袂及第,舒元舆为东阳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宰相身份的人物;厉、冯、舒与中唐崛起的滕氏合称“四大望族”。唐代东阳科举人物都出现在这四大家族中,别的家族恐怕连梦都不敢做。
可是这一切,后来都被黄巢给毁了。“天街踏尽公卿骨,府库烧为锦绣灰。”(韦庄《秦妇吟》)黄巢二次杀入长安,几乎杀光了满朝公卿,门阀士族势力就此走向消亡,从此进入平民时代也就是打工仔的时代。那份与生俱来的骄傲找不到了,热情进取、高调退守的人没有了,集悲凉慷慨和缠绵婉转于一身的人也没有了,能发出身世之感、宗国之哀的轻艳诗人消失了。从此相逢不问出身,点头便是哥们。于是一种更自由、更能反映内心动静和情感寄托的诗体——词,走到了前台。我们看宋词元曲,明清时代的诗词,更多是个人的诉求。
国家风雨飘摇,士族和寒门一样都朝不保夕,一切都被晚唐的诗歌所记录,读前面韩偓的诗歌也是生死由命,但士族的那份骄傲没有丢失,不管生活在哪个时期,家国情怀一直都是唐人的主题,没有个人的哀怨,没有玉石俱焚的牢骚。我举三段词句,大家用心体会下。
人人尽说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。(唐末 韦庄)
帘外雨潺潺,春意阑珊。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,一晌贪欢。(南唐 李煜)
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(宋末 蒋捷)
同样是倾诉末世的个人遭际,同样是健笔写柔情,韦庄落寞的胸怀是哀而不伤。
唐诗的那份从容是刻在骨子里的,唐人的那份伤感也是与生俱来的。我们为什么喜欢唐诗?因为我们身上最缺乏的就是唐人才有的那份从容和感伤。至于宋词元曲里的内容,纯粹是个人的悲欢离合,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,可以感染,可以享受,然终究是没有距离,缺乏神秘感。
天真是唐诗最令人心动的特质
门阀士族没了,我们的性格也随之丢掉了一份至重的性情——天真。
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(王维)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”(高适),换作你我,大漠落日,可能早就心生畏惧了。唐人就很天真,“卷舒开合任天真”(李商隐),唱着歌出关去了。
最能反映唐人天真的是柳宗元的《渔翁》:“渔翁夜傍西岩宿,晓汲清湘燃楚竹。烟销日出不见人,欸乃一声山水绿。回看天际下中流,岩上无心云相逐。”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形象又写意,只闻其声,不见其人,以自适之情放歌于山水之间,哪还见得尘世之心?有人认为此诗后两句像盲肠,不要也可。一首歌行体,裁作绝句,跟宋人写的一般无二。明清时期有些选辑就干脆自作主张弄成了绝句。苏轼说:“诗以奇趣为宗,反常合道为趣。”柳宗元的诗本来走的“奇险”一途,和宋诗差别不大,这么改后人也没有大的意见。苏轼的话也是为宋诗作总结。诗离不开诗人所处的时代,在宋人看来,诗到前朝就做完了。这话鲁迅也说过,眼前就只剩下“奇险”“奇趣”一路,反常而能合道就行。然柳宗元是生活在唐朝的诗人,“奇趣”在那个时代来说,不是正经路数,所以有后两句才见本质,是那个时代浸润的产物,是率真超然。诗歌不达到这个境界,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东西。在诗歌来说,超越这个时代的东西是没有的,它一直在路上。
现在再读唐诗,就要充分理解唐诗的那份“天真”,诗歌写到后来是越来越自我,很难得见唐人的意趣了。唐人惯用实字,实字需要用心去支撑,这个“心”,是家国情怀,家国休戚与共的使命感、责任心,把自己放在最高处,恪遵天命。这就需要保有一份天真的初心。读唐诗一定要读到这个份上。
为何说一切好诗到唐朝就做完了?因为后人失去了那份骄傲,那份安宁,那份天真。
常建的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,最受人激赏的便是“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”,欧阳修几次想仿写,终因无法超越而放弃。但在同时代的唐人看来,这不过是笔性墨情而已。唐人自己更喜欢“山光悦鸟性,潭影空人心”这一联。借冯友兰的话说便是没有洞见,没有玄心,又如何能抵达唐人深处。
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门阀士族早已没有了,但古人的那份天真,“一往有深情”(《世说新语》),我们还是可以培植的。回到唐代去,“天然去雕饰”(李白),就要把自己当成孩子。我们说要爱国,但用文字来表现爱国主题,近100年来都写得很肤浅。看唐末的诗人,哪有一个怨天怨地怨国家的?被风卷倒了,就收拾心情,重新站起上路。
“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”,风气需要一些人去带动。
最后,送大家一首我写的诗:“坐听山有月,起看水无声。映竹风千度,居高浪一层。”前两句出自王维“远看山有色,近听水无声”,我反其义,突出“心”和“悟”。你眼里的千变万化,在菩萨看来,都不过是心在动。大风吹进竹林,场面何等壮观,然在上苍看来,不过是连绵山势的一部分而已。心不动,万物皆不变,你才能成主宰。
那我们为什么忍不住心动?因为唐诗在那儿。
编辑:严格格
二审:董之震
终审:单昌瑜

歌画东阳 共见精彩